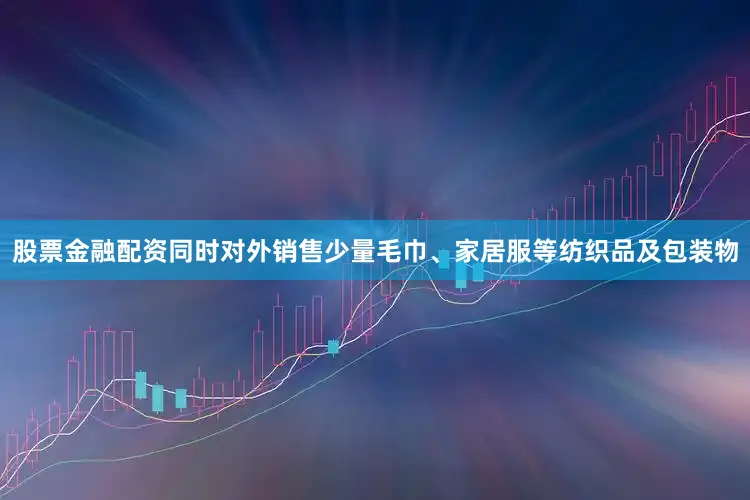公元前473年,越王勾践出师伐吴前,豪壮投酒入河中,与三军将士共饮,誓要一雪会稽之耻。以“一箪之醪”提振三军士气的美谈,赋予绍兴这条小河“投醪”之名,也让它成了越人精神的历史见证。
两千多年后的投醪河畔,一场秋雨落在稽山中学的考古工地上,将燥热了一个夏天的土层浸湿。粗大的木构、清晰的墨书、叠压的井台……庞大的建筑基址面貌渐展,一段段经久沉睡的越国记忆次第苏醒。
遗址内的木构材料经碳十四测年,距今约2500±30年,恰与《越绝书》记载的公元前490年勾践命范蠡筑城为都的时间完全吻合。传说中的越国王都不只停留于文字,而是真真切切存在过。这里有过帝王将相的传说,也有过金戈铁马的壮阔,更带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温度。
绍兴稽中遗址内,战国时期越国和汉代高等级建筑基址 图源:“浙江发布”微信公众号
一
展开剩余84%《越绝书》中,越人与水有着密切联系:“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,往若飘风,去则难从。”这段文字描述曾是我们对古越国最直观的想象——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湖沼河网间,在潮湿多水的环境中生产生活、自给自足。
然而,纸质记载总是隔着一层薄纱,直到稽中遗址出土,越国“与水共生”的模样才变得清晰起来。
遗址之中,最令人惊叹的,莫过于那些保存完好的战国木构。纵横交错的“筏状地栿”,以圆木间隔叠压成基,既御潮湿,又承重压,是古越人面对湿地“生存困境”的创造性解答。
没有巨石金玉,越人便以栖息地的林木为材;没有北方夯土之利,便借助水的浮力与木的韧性,在泥沼中筑起城垣官署。这些地栿之上,曾矗立着越国王都;而越国基址之上,又叠压着汉代的郡县官署——“山阴丞印”封泥、“会稽郡壁”铭文砖皆出于此。封泥作为古代官方文书的“保密标签”,印证着这里或许曾是山阴县官署所在;“壁”字铭文的砖,早期只为皇宫或官署所用,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,预示着遗址与汉六朝时期会稽郡治密切相关。
绍兴稽中遗址出土的地名遗物 图源:“浙江考古”微信公众号
水是江南的挑战,亦是江南的馈赠。遗址中23眼水井中藏着的,不只是清泉。若干井底出土了大量瓷器,精美却凌乱,似是在某个兵荒马乱的日子,被慌忙避祸的豪门大户匆匆投入井中,盼太平之后重取。谁知这一别,竟是永诀。
当时间线拉回至现代,今日考古队员的守护,又何尝不是另一种“与水共生”?
考古界有句话:“干千年,湿千年,半干半湿就半年。”遗址中大量木构在水中浸泡千年,才得以保存下来。但这也给发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,泡在地下千年的木头一旦暴露在空气中,那些脆弱的木构就会像泡发的千层酥一样,一碰就碎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,考古队员搭建防雨棚,用喷淋为基坑降温,围绕遗址建设防渗墙,24小时不间断地抽水、补水来回作业。为了保持木构件的适宜湿度,工作人员同时用喷雾器精准有效地润湿木构件,24小时轮班给木头“敷面膜”,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。
2024年7月23日,考古人员在绍兴稽中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发掘出的木质建筑构件 图源:“绍兴古城”微信公众号
二
在《说苑》所载《越人歌》中,越人船夫对鄂君子皙这样吟唱:“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说君兮君不知”,展现了一个虽因“鴃舌鸟语”而语言不通,但情感丰富、文化独特的民族形象。
而在稽中遗址的瓦片上,依稀又有着另一类越人声音,让我们思绪万千:谁将心事付瓦片,瓦上文字有谁怜?
一片汉六朝时期瓦片上,墨迹斑驳:“二百斤交了”。字迹歪斜,却流畅自然,似是一气呵成。也许是当时的一位小吏刚核完税目,吁一口气,随手捡起瓦片记下这一笔。那一刻,他可能想着家中的晚饭,可能嘀咕着明日的差事,却不知这一笔竟穿越千年,又被后人轻轻拾起。
另一片瓦上,“会即下受役众”六字,宛若穿越时空的叹息。学者疑“即”为“稽”的简写,或许因为记录者识字不多,却情急智生,以简笔字抒发己意。寥寥数字,道尽劳役之重、身不由己之困。
这些瓦片本是官署建材,却成了古人随手的“便签”、意外的“日记”。它们不是史官笔墨,不经修饰、不求传世,却正因如此而显得格外真实。文字之下,是活生生的人,铭刻下的是他们的疲惫与调侃、无奈与幽默。
稽中遗址之所以动人,正因它让我们看见,宏大历史之下,尽是平凡人生。他们纳税、服役、祭祀、避乱、书写、建造……于浩荡的历史长河而言,那些史书之外的平凡人的生命或许短暂如萤火,却共同勾勒了一个时代的万千形态。
绍兴稽中遗址内的越国马坑 图源:“浙江考古”微信公众号
三
遗址的西北角,一匹骏马遗骸静卧泥土之中。考古专家推测,它或是战国时奠基祭祀之牲,以祈求建筑顺遂平安。遥想它曾毛色光亮、嘶鸣清越,在一场仪式之后,默默守护了这片土地两千余年。
出土的甲胄之上,刻有“大鎁师傅王”五字。这是工匠的留名,还是某位将军或显贵的专属标记?我们已不得而知。另有一枚写有“弟子会稽张龙 诣门下 山阴字伯龙”的木刺,则应该是一张递出用于社交的名片,轻轻飘落于历史缝隙之中。它不属于王侯,而是来自一名寻常士子,因缘际会得以诉说一段微末却鲜活的过往。
越地多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,何来如此雄骏之马?“鎁师傅”究竟是何人?“勾践王宫”又隐于古城何处?有些谜或许永远无解,但正是这些空白,让历史充满想象与敬畏。
“夫剪发文身,错臂左衽,瓯越之民也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这样介绍越人,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也提到“越人断发文身”,这些对越人不同于中原穿着打扮的外形描述,多少带着些许偏见。而稽中遗址的发现,让我们重新认识越地文化——它是有着独特价值、充满地方智慧的文明。此地“与水共生”的智慧,那些宏大叙事下普通人的生活韧劲,经历数千年依然温热。
今天的绍兴人,仍在延续着越文化的基因。老城区的台门建筑、水乡的河埠头,乃至干事创业的坚韧和激情,都与遗址中展现的越人精神一脉相承。正如当地一位老人所说:“我们绍兴人骨子里就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头,这恐怕是从老祖宗越王勾践那里传下来的。”
考古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。它让我们学会俯身倾听——听木构的呼吸、井底的回响、瓦片的呓语。它们无不在告诉我们,文明不仅在庙堂之高,还在百姓日用之间;历史不只是井然有序的帝王谱系,更是亿万普通人活泼泼的生命足迹。
稽中遗址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,让我们瞥见了一条时间的暗河。在这片土地上,历史源深流长,不断绵延生长,那些穿越古今的笑与泪、坚定与挣扎、失去与希望,无不浸润着历史的馨香,更多有关这片土地的故事尚待我们去发现、去认识、去传承。
本文播音:洪放
声明:稿件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。
发布于:北京市升阳配资-安全杠杆炒股-券商配资-a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